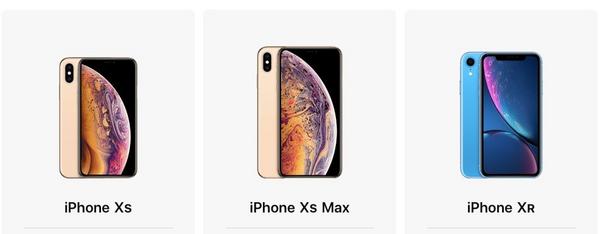關於雲端裡的雜訊
2022/06/29
最近又開始聽見許久不見的,腦中那個孩子微弱的喃喃自語。聽起來總像十多歲出頭的聲音──這麼多年來都還在一樣的年紀。他反覆說著相同的模糊語句,只依稀聽得見其中的幾個字詞:「要…離開……找到……的地方。」是個要逃家的孩子,總嘗試從什麼之中掙脫,每每聽見時都這麼想。而他近期的再次出現不禁令人擔憂著這一段時間以來的改變將會消失並回到原樣。彷彿先前這段時間的嘗試都屬夢境,醒了以後會是一如既往的霧濛濛。
其實打從個位數歲數時,那個聲音的內容就一直存在。起初用無聲的形式縮藏在大腦一個小角落,隨著年紀增長,它開始有了自己的聲音(也就是那個十多歲孩子的聲音),也越長越大。雖然不至於到奪去主控權,但確實必須在學習共存這件事情上花一些心力與時間。忽然想起幾年前大多時候仍對於它的出現處於驚慌的狀態。畫面裡汽車後座上的乘客面無表情地說著「家不一定是歸屬」的話語,縮藏在表皮下的我卻不停顫抖。然而,那些話其實是如同灌飽氣的袋子就算捏緊封口,卻仍從下方的破洞漏氣的那種不可控與無計可施。話語就是以那個孩子的聲音作為推動力,從唇齒間失控地洩出…再也收不回來。那是第一次感覺到它凌駕於我。儘管短暫、瞬逝。
可它終究是個孩子。那些話語終究是一些最單純而直接的感受之下所給予的回應。然而,頻繁說話的時期也有靜默的片刻。根源性的事物裡頭最終還是有著令拉扯與掙扎存在的要件。
那天是她的入土儀式。延宕了快兩個月,照理來說應該在離世的一年後進行。過程中精神恍惚,多數時候並沒什麼感受,僅有一些不帶起伏的思緒在腦中運作。看著眼前金爐裡的火焰,我想起該日的天空與雲況。她的招魂旛被拿走之前下著雨,天很陰,拿走後在前端竹支點上火,燒起來後天空的雲退出一個缺口,露了點光。招魂旛被燒盡後,那個缺口消失了,再一次烏雲滿佈。後來儀式結束後要帶她回家。我抱著她的相片,左邊放著骨灰壇,坐在車子的後座右邊──以前她最常坐的位子,然後我把照片抱得好緊、好緊。現在是一年後了,那幀裱框的大頭相片擺在獨立貢桌前,明明是她,卻不像她。永遠記得那天,我覺得自己真正地、終於被徹底抽空了。「他們⋯都離開了。」那時候十多歲出頭的孩子靜默地像消失了一樣。明明他應該想著自己能幾乎沒有羈絆與掛記的逃離。
去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檔案還停留在同一個進度,裏頭仍然是雜亂的碎文句。曾在心裡許諾她,待我再次拾回平靜便會將那些散亂無序予以編排和安放。然而,至今卻仍將那些狼藉般的情緒困侷在文件之中。後來才理解,原來那些羈絆的實體消失,一定程度上都促使真正的脫離變得更加困難。對其他對象的掛記與顧慮在這些失去之中,只會疊加與增長。所以孩子後來才不說話了。
從小就喜歡看雲,最常坐在行進的車裡,仰著頭看窗外天空中雲朵的變化。會在腦海中編排無數個故事,依照每個雲朵的形狀分配給它們不同的角色。高中的時候──那最不該有空閒被浪費與揮霍的階段,拋棄一切身分責任地,躺在司令台看無邊際的天空裡的雲。是一種創造時空餘裕,甚至是無時間性的方法,大概是那時便開始學會做這件事。看雲的時候將自己的意識與靈魂放置在眼睛和雲之間的空域。那裡輕盈得像漂浮在水面上。雖然這於行為表象是一種漠然,又者是追求逍遙、無拘無束的想望之表現,但只要在那個十多歲孩子仍存在於我之中,那些雲在視野裡終究會存在雜訊與顆粒。始終無法純粹而清澈。 「那是灰灰藍藍…帶有顆粒感的顏色。」後來終於明白他人所給予過去的我的顏色象徵,終於找到顆粒感的來源。它們確實有著干擾性質,卻也並非真正是一種干擾──習慣讓它們不刮眼睛、不弄疼傷口,所致最終的沒有感覺。想逃家的孩子還是一直說話。在看雲的時候仍不停地喃喃自語。「要…離開……找到……的地方。」微弱,卻在內容上始終堅定。所以其實那時候的雲裡就有顆粒般的雜訊了。更或許在小時候由車窗看出去的雲朵角色,便也早已在無意識的區間內參有雜質。
後來更加猖狂地看天空…連行走時都抬著頭,讓自己和天空平行,讓雲朵代替掉視野前方迎面而來的人們。無法是純粹的漠然,而是參雜許多拉扯與缺乏實踐可能的,對無拘無束的想望,卻仍然是在不可控與無計可施之情形裡頭的最大自由。「那是無所作為裡的消極中最大的積極了。」十多歲的孩子繼續微弱的呢喃著,最近的頻率更是高出許多。
在最樂觀的狀態時曾想過讓他消失,儘管過去在學習共存上付出很多心力。直到已經噤聲許久的狀態再次被打破,如同當頭棒喝般忽然明白某些事物終屬於根源性的。那個十多歲的孩子就是拔除不了的根,纏繞在精神基底上,由此之後的雲都必須將顆粒般的雜訊視作一種正常與和諧。「要…離開……找到……的地方。」這必須成為吸吐氣般輕盈而自然的存在。
還有其實,我一直很想知道,招魂魄燒盡,空中的雲合起來以後,究竟是什麼進到裡面了?是從我身上被割下的些什麼嗎?是她嗎?那我還有機會見到被收納在空洞裡面的事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