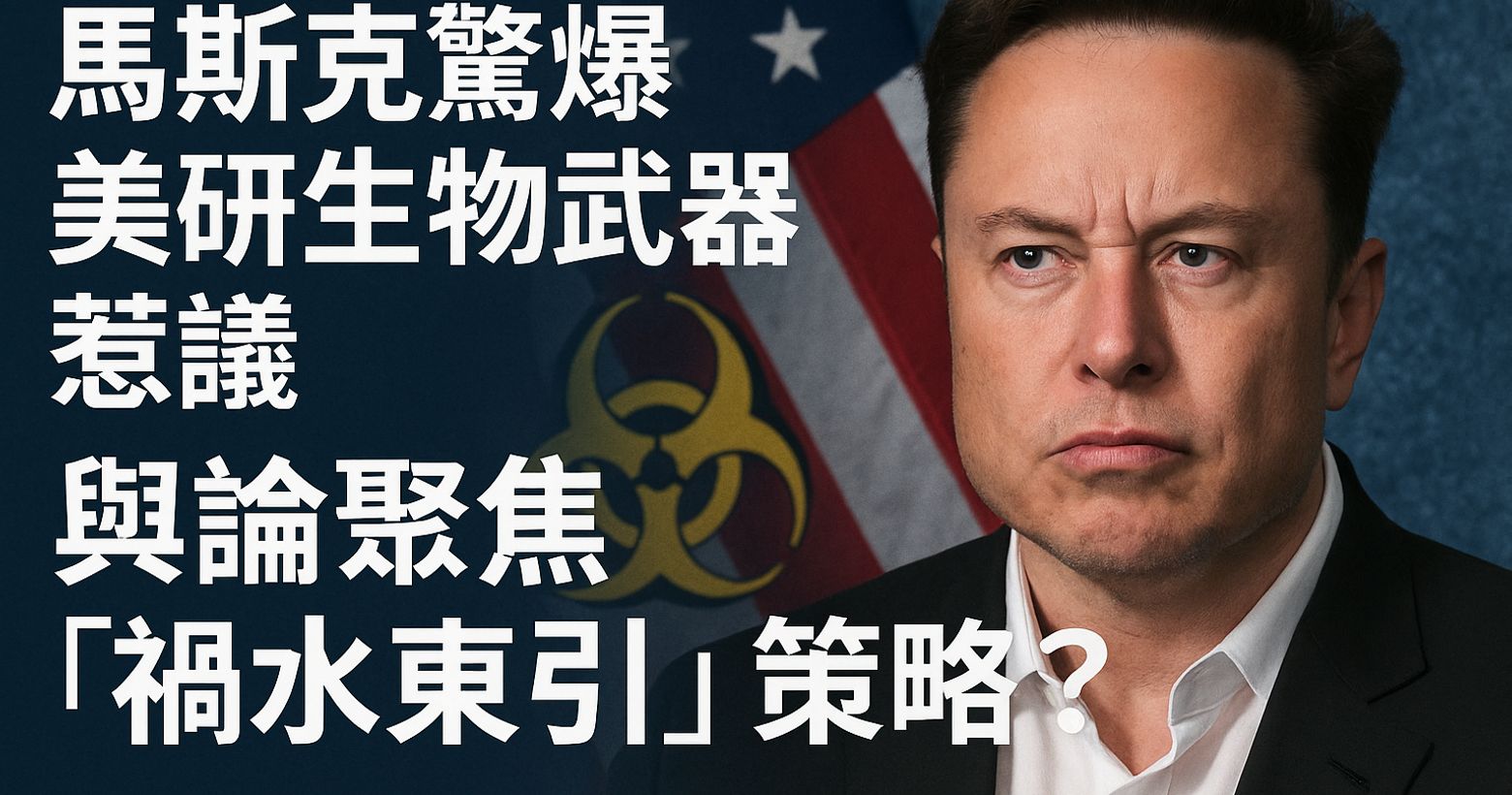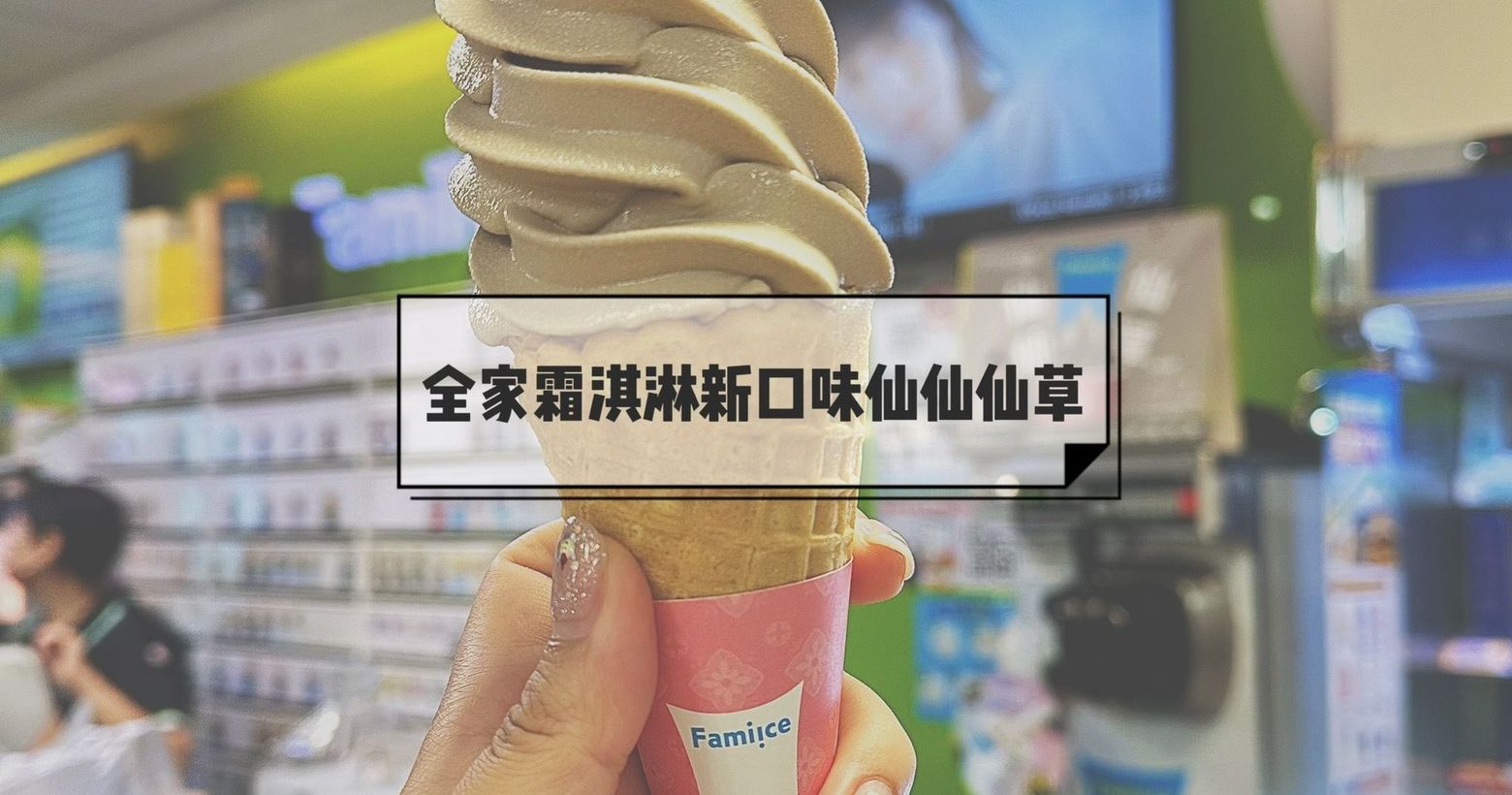🎥🎞️📝《可憐的東西》| 我是個怪物,那你呢?
《可憐的東西》除了是一部以女性主義視角看見女主角「貝拉」成長曲線的電影,同時,也以貝拉的唐突行為直面地戳破當代社會的媚俗。
《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的同名原著小說背景取自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在這個工業發達的 19 世紀,最被受整個社會壓抑的正是「性」,任何跟「性」有關的話題都被社會高度檢視和規範。


如此廣泛的性壓抑深植於當代許多生活層面,就連精神分析的創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其學說也主張「人類一切的生活動力是基於對自身性欲的壓抑」。有人曾開玩笑,如果你夢到棒狀物,佛洛伊德會說「那代表你對男性的陽具有極度的渴望」。(不盡然錯,但確實過於斷章取義)
╴
貝拉有著成年女性的身軀,卻裝載著尚未出世的嬰兒大腦,她的身體受到維多利亞時期的規訓與調教,然而,她的認知卻處於完全自由的隨興,不受社會桎梏地且恣意地展現自我。


一個大談性欲的女性,也許會被說成是蕩婦(電影甚至說是惡魔),反之,一個大談性欲的小孩,也許會因涉世未深而當場被糾正。《可憐的東西》巧妙地結合社會上兩種不同期待的個體:一個大談性欲的巨嬰,該如何評判其行為?
透過貝拉的視角,反而看見那時的倫理荒謬:
持守婚前守貞的未婚夫,卻接受曾賣淫的貝拉;自稱藐視社會規範的「性愛大師」偉德律師,卻受不了貝拉當眾大談他的床上表現;為了科學奉獻一生的巴克斯特博士,卻也因為科學而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而貝拉,卻「極度神智清醒」地說著「極度不被接受」的事。「我現在需要錢,而剛好和男人交歡會有報酬,那麼為何不去呢?」貝拉毫不猶豫地答應妓院老鴇的邀請,成為青樓女子的一員。
那麼,相比起直言不諱的貝拉,自由地被社會大眾譴責;那些堅守個人節操,卻因而畫地自限而困於社會規範的人,誰更像是「可憐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