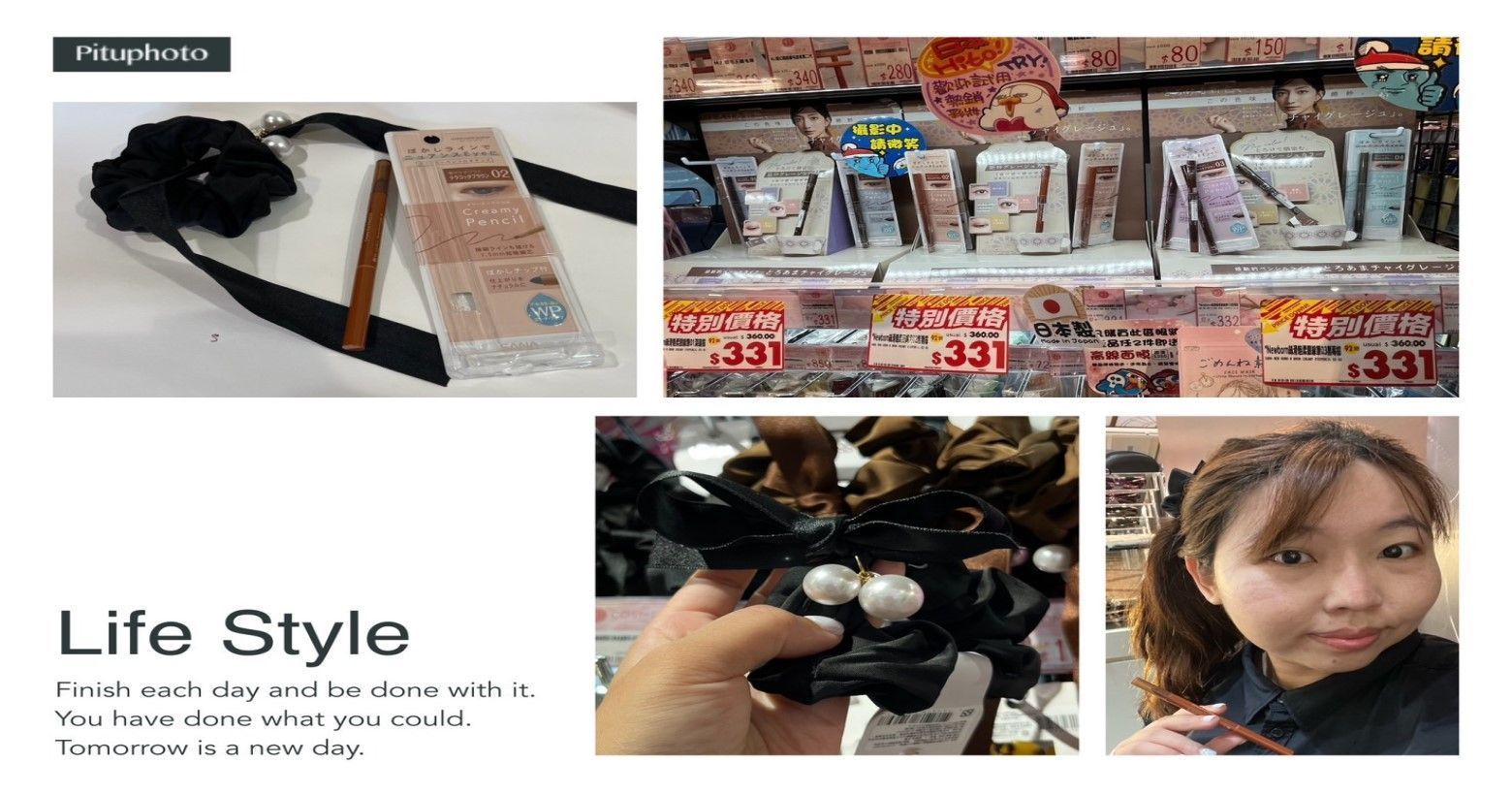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在死刑定讞之後
今天要來介紹一部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這部片是由李家驊導演所拍攝,入圍了本屆台北電影獎和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這部片的拍攝過程並不順利,由於題材敏感,以及台灣社會普遍對於死刑定讞的受刑人有著不諒解的心態,經過四處奔走籌資、甚至自掏腰包才完成。幸好有拍攝團隊堅持不懈,民眾才有機會看到這部片,才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死刑」到底是什麼?
☆前方有雷,若想保留觀影樂趣的讀者,請先看完電影再繼續閱讀!☆
本片共分為三大段,分別介紹了三位死刑犯的案情,以及從他們的家人、接觸過他們的律師、廢死聯盟的人員口中,拼湊出的「故事」。第一位是殺害自己國中同學的連佐銘,第二位是砍殺父親一百多刀的陳昱安,第三位是捷運隨機殺人的鄭捷。
三個受刑人中,只有第一位死刑犯尚存於人世,也是唯一一位在死刑定讞後十幾年,家人仍然持續會去接見的受刑人;陳昱安在獄中自縊、鄭捷在2016年5月伏法。
畫面從坐公車前往看守所的路程開始,到了接見室,雖然父親的面貌被霧化處理,但這十幾年來,街坊鄰居恐怕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兒子是殺人犯,一路以來承受的壓力,又豈是電影中一個模糊的影像能夠帶過?
下一個畫面,看守所中的連佐銘提到,自己在監所內開始學下棋,訪問者問下棋是否有改變了他的心境?連佐銘說,自己變得比較會去思考,以前遇事情比較衝動。那當年的案件是一時衝動嗎?連佐銘苦笑:不是一時衝動,很多事情都很衝動…
辯護律師說,連佐銘和被害者是國中同學,知道他家裡開銀樓。連約了被害人出來拚酒,被害人醉倒後,連佐銘殺害了被害人,把屍體跟車子丟棄後,向被害者父母要求贖金,後來在取贖金的時候被警察逮捕,這才供出自己已經將被害人殺死。一審的法官判決是殺人罪,說連佐銘是預謀殺人,後來才改判為擄人勒贖,死刑定讞。
訪問連佐銘,當初是預謀殺人嗎?連佐銘說,我現在就算解釋說我不是,你們也都還是認為我是預謀犯案。
連佐銘說,當天喝醉後口角,殺害了被害人,眼見鑄下大錯,當時只有二十歲的他,不想被抓去關,也不想連累家人,唯一解就是跑路。跑路需要什麼?當然是需要錢。打電話向被害者家屬勒索後,他一路茫然騎著車,回過神來時,已經騎到了桃園,他要求被害者家屬將贖金放在那台他騎的機車上,於是被警方循線逮捕。現在回頭看,這實在是相當沒有計畫,未經過思考的行動,真的是預謀嗎?
這一錯再錯的選擇,在旁觀者看來很不可思議,但是如果設身處地,我們又能要求國中畢業的連佐銘,做出什麼更聰明的決定呢?
連佐銘形容這十幾年來,自己每天早上醒來,都像是家裡發生火災一樣,什麼東西都被燒光了,自己一無所有,是個沒有未來的人。年幼的稚子每次去看他,都天真地問爸爸:「什麼時候會出來?」連佐銘總是說:「快了。」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這樣的茫然和絕望感,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
第二案中的陳昱安,殺害的是自己的父親。
隔代教養的陳昱安,從小受到祖父的疼愛,後來被接回父母家住,父母的管教相對嚴格,而陳昱安長大後又不願出外工作,宅在家裡打電動,讓陳父憤而將他趕出家門。因此心生不滿的陳昱安,遂計畫要殺害父親,他還預先寫下計畫並演練,在父親下班回家後對父親行兇,共砍殺父親一百餘刀。
陳母對陳昱安亦相當不諒解,她表示陳昱安若是出監,一定會回來對其它家人行兇,屆時將會血流成河,故她向法官表示,希望一定要判處陳昱安死刑。
因為手段兇殘、且事後陳昱安表示自己並不後悔,且行兇時意識清楚,最終被求處死刑。
陳昱安曾經因為精神障礙求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及有高自殺風險,其就診紀錄顯示他曾經找到一份保全的工作,但是最終被辭退,因為雇主發現其有精神障礙。不過陳母表示,陳昱安的精神障礙,是他為了逃避兵役自己去申請的。
第二案的片段中,並沒有訪問陳昱安的親屬,而是訪問了廢死聯盟的員工以及陳昱安曾經的辯護律師。透過他們的敘述,我們彷彿看到了弒父人魔的另一面。
陳昱安在寫給廢死聯盟的信中,提到自己對家人的恨,他表示父親管教嚴格,且不准他去交朋友,父親說:「有弟弟就夠了,為什麼還要交朋友?」雖然外人難以評斷家務事,但是從陳母的說法中,家人似乎並不認為陳昱安的精神障礙真的對他的生活和社交造成了影響,僅僅認為他是為了逃避兵役而裝病。
或許陳昱安的人格原本就違常,但是從小被祖父溺愛而缺乏面對挫折的能力,精神障礙影響社交、找工作碰壁,以及不被家人理解的痛苦,是不是都可能是造成今天這個悲劇的推手?
陳昱安在看守所內持續看診精神科,但因為死刑定讞的受刑人是不會作業,也不會有勞作金的,所以陳昱安積欠了看守所不少醫藥費,家人完全斷了聯絡的他,常常向廢死聯盟以及辯護律師求助,希望他們能夠給予金錢的支援。兩人都不約而同提到,每次去見陳昱安,他看起來都非常興奮,在外人眼中泯滅人性的他,還是非常希望有人能夠關心他。
最後陳昱安在看守所中用橡皮筋自縊,這樣的死法相當痛苦,顯見他死意堅決。沒有人知道他在最後一刻心裡在想什麼,或許是因為死刑讓他看不到明天,或許是因為久病讓他厭世,又或許是因為他真的太過於寂寞了。
第三案,是震驚社會的「捷運隨機殺人案」。
鄭捷於2014年在台北捷運對民眾無差別攻擊,造成了4人死亡及24人受傷,被判處四個死刑,最後其於2016年槍決。
關於鄭捷實際上犯案的動機,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家境優渥,但是父母疏於關心,所以造成他性格扭曲;有人說他小時候其實個性開朗,但是喜歡一些暴力殺人的漫畫故事;他亦曾經在網路上發表自己小學時就對兩個女同學心存恨意,立誓長大後一定要殺了她們,其網誌中也有多篇自己幻想中的殺人場景。
鄭捷犯案後,對於想幫其辯護的律師,態度也相當防禦、冷漠,也給外界一種毫無悔意的感覺。我相信這世界上有純粹的「惡」,有些人天生性格就不一般,缺乏同理心,會透過傷害他人來得到樂趣,或許旁觀的人們一直試圖要去剖析這類人的心理,是希望能藉著了解成因後,預防再有有人因此受傷。但是從古今中外對於殺人狂的研究,恐怕有些人是無法通過教化來改變的。
因為鄭捷從犯案到伏法只有僅僅兩年,我們無從得知他真正的心路軌跡是什麼?也無法得知,他到底有沒有「教化」可能。
這一案中,我想著墨的並不是鄭捷本身,而是鄭捷父母在被害者頭七那天,出現在捷運站,對著媒體下跪道歉的畫面。
從鄭捷父親所發表的言詞,就不難聽出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你很難想像這樣的家庭,會發生這樣的憾事。鄭父顫抖著聲音,代替兒子向被害者道歉,並表示自己心也很痛,但是鄭捷必須為他做的事情付出代價。畫面中另一個是沒有出聲的鄭母,兩人對著鏡頭跪拜的畫面,令人很難不鼻酸。誰會希望自己養大的孩子,成為人人唾棄的殺人犯?而且他們永遠不會明白,到底自己是哪個環節做錯了,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鄭捷的辯護律師提到,鄭捷表示,律師想要怎麼做都可以,但唯獨希望他們不要去麻煩到他的家人,而鄭捷父母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也幾乎沒有出面。律師一開始有點不諒解,對於這個案件,為什麼鄭捷父母表現如此的不積極?後來他明白了,對於整個社會排山倒海而來的譴責和壓力,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是無法面對的。
鄭捷被槍決後,為了躲開大批媒體,殯葬業者用了調虎離山之計,讓鄭父悄悄地去認領遺體。看到遺體後,鄭父當然相當地難過,但鄭母並沒有出現,最後殯葬業者打通了手機,將電話放在大體的耳朵旁,讓媽媽對鄭捷說完最後的話。
這部紀錄片並不是想要幫加害者平反,說他們殺人是對的,也不是要下任何「應該廢除死刑」的結論,只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讓閱聽者能夠知道,這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一種看事情的角度。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那些十惡不赦的死刑犯的心路歷程有什麼了解的必要?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同樣的成長背景,也不是每個人都會犯下罪行,沒有值得同情的必要。但我想說的是,我們之所以拒絕了解那些死刑犯,背後真正的原因,會不會是因為,如果我們去了解了他們的無奈,我們就沒辦法真正地憎惡他們呢?會不會當我們發現他們也只是跟我們一樣有愛有恨的普通人以後,我們對善惡分界的那把尺會動搖,我們會難以決定自己該相信什麼呢?
對於受害者,我們充滿了同仇敵愾的心,卻忽略了加害者家屬,心中也有許多難以言說的悲痛。他們除了也失去了自己摯愛的親人,更要一輩子背負著不被社會諒解的枷鎖,心中還有無盡的疑惑,永遠也沒有解答。就像是「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李曉明的家人亦是單純生活的平凡人,卻因為其犯下的罪行,全家跟著被判刑。
導演李家驊提到,這部紀錄片中三個死刑犯的家屬,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家屬態度,有的不離不棄,有的斷絕關係,有的遭受巨大壓力難以面對。
身為監所管理員,我能體會若要管理死刑犯或重刑犯,都是相當艱辛的。因為這樣的受刑人對未來沒有希望,知道自己即將老死在監或者有一天就會被執行槍決,很容易讓他們產生厭世感,造成高自殺風險,但監所又不允許他們自殺。如果死刑總有一天要被執行,那麼他們的自殺為什麼要對監所管理員究責呢?
若是廢除死刑,改判以有期或無期徒刑,我必須說,有些受刑人並不會因為教化而改變。在監所內,我看過許多偽善的受刑人,教誨志工相信自己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心志,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人在監內將會成為一大戒護隱憂,這也是現行監所人力不足之餘,所迫切面對到的問題。
至今,對於該不該廢除死刑,我始終沒有答案,但我希望透過這樣的紀錄片,讓更多人願意去思考這個議題,無論正反,有理性的討論,才會有更多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