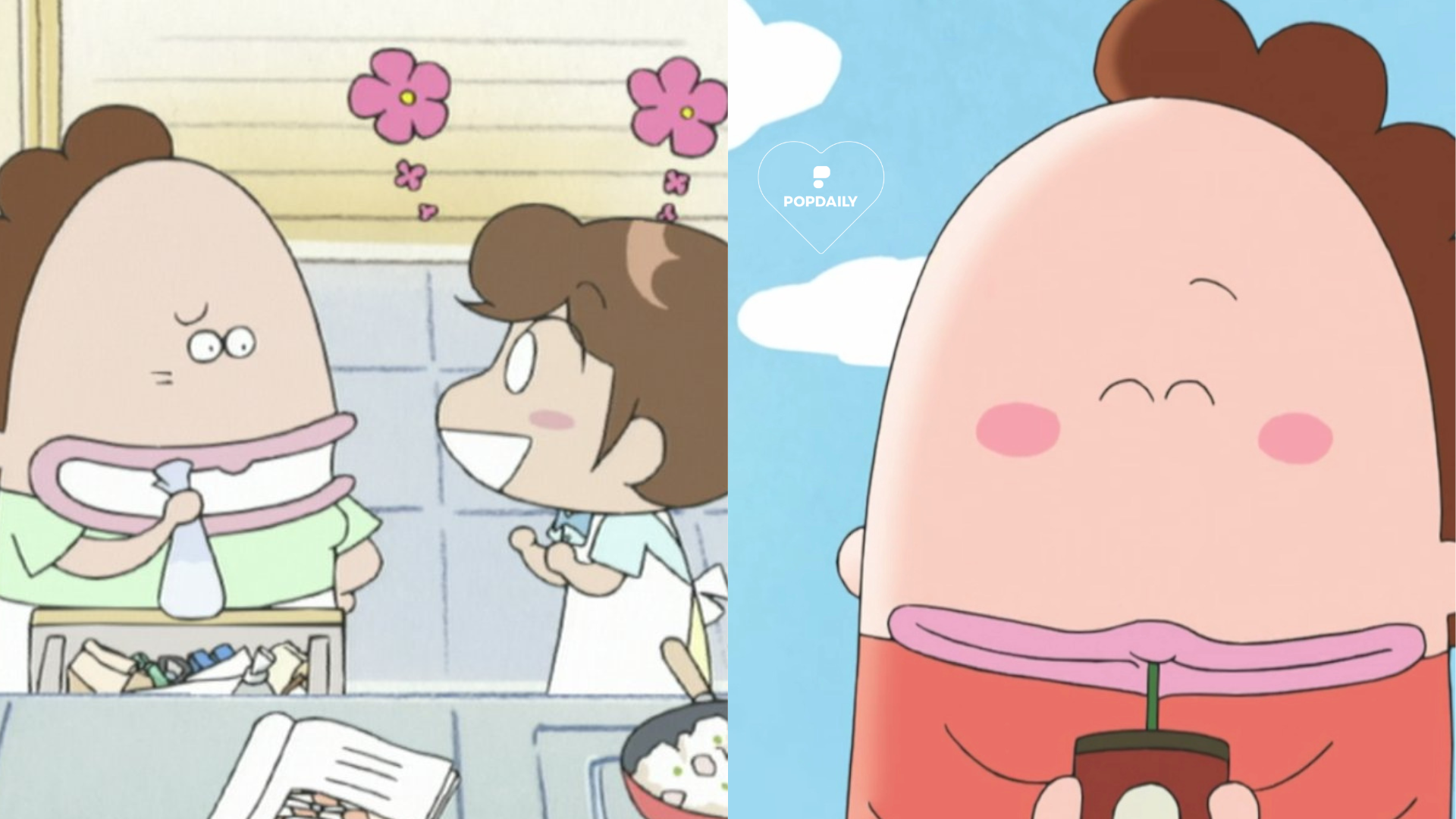關於平靜底色
2025.03-05.15
前段時間寫了無數破碎的文句段落,大多較像是宣洩和排解,將一切事物吐露、表達、紀錄。毫無系統亦無整頓勇氣的情況下,那漸漸堆積成無可負荷的情緒碎片,那樣巨大卻無法被梳理的存在,壓迫地成為生活的阻礙,至最後我終究還是停止了書寫。
那些時日裡的絕望,大多是源於信念的瓦解,由身邊親近之人的改變而產生的質疑,使我認知到人人的自我都在膨脹,並且得以輕易排擠掉一切阻礙於前的事物。他們所謂的理性與抱負在我看來都是發脹的ego ,以及精神性的迷失——如黑影般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我惶恐地逃,更因此失去對全人類潛能的信心,發覺愛的力量在萎縮,驚覺這般絕望的處境令我無法再對未來人類的展望抱有無可動搖、不容質疑的信心。他們的話語像毫無人性的猛獸低吼,我見不著一絲歸屬,更時常對眼前的情境感到反胃。
然而,當存在變得危急單薄時,僅有文字能令內心覺著踏實穩妥,像是自我之於世界或宇宙的錨,深深嵌在我以外的他處,成為存有於世界的一絲依連,堅固、不可挑戰、不存在悖論。
如果人的焦慮不安始終是源自與世界的隔離感,而對於自己的存在感到惶恐,那麼取消該區段的隔閡,即是找到「被拋擲於世界」的事實之同時也存在的錨——即與世界(或人)的連結物(點),是感受到回歸世界的做法。於是寫不出文字的我握著書,找著存在、尋著安心。
這兩個月包裡總放著泰戈爾的The Religion of Man,一本珍貴的經典,新潮文庫,民國77年的再版印刷,輕巧泛黃,是D一讀再讀後傳承給我的文字。南下北上的火車上,捷運通勤的路上,午休時間在二手菸菸霧繚繞的17樓屋頂天台上,這些文字都在陽光下閃著金光,也點亮了心裡某些極致頹靡的信念與意志。
那種救贖如在夜裡的馬路上轉圈跳躍的輕盈,如自己的身體在葉縫間陽光灑落之際分散,又如徜徉在藍天的寬闊,甚至是化進一朵溫柔的雲的包覆與安全。靈魂平靜又磅礴激昂,意志在溫柔與希望下融化,抵達一種既飄散又踏實的合一狀態。
這與二月底在都蘭觀海時獲得的體會相重疊。
回台灣後短時間內去了兩次都蘭,那塊土地與那片海也意外地將心裡某些以為永遠無法彌補的瘡口修復、安撫了一些。雖然還是不清楚「自己成為自己的海」的前提下,應該找尋如何的天空相互接連,但那些感受性的確認、原始性情慾的流動、超越言語的自然連結⋯都讓我確信有些事情仍舊在崩塌後,於精神內涵上永垂不朽。衰亡的永遠只是表象,而死亡從來都只是外在性的死亡。
於是,這段時間便是不斷地和解,與無法獲得正當解釋的往事、與難以往懷的體驗、與他與你與所有人、所有關係⋯⋯其實全都是與過往的自己和解。我終於找回那些消失的感覺以及過份充沛的情感,更是在被動式的積極裡再次感受到自己成為大生命體的一部分:我是他,我感覺到他,他也令我理解他。這些體會的成形將我從深淵般的絕望中釋放,鬆開緊握的雙手,為了不再讓過分的力道導致失真,為了激活頹靡的精神、收聚發散的愛的能力。
後來我也理解並不是非得有個桅杆作為信仰,因為信仰作為一種涵納世界的眼光,於空間上理應是無限制與邊際的。精神的流動性應該被保留,避免教條化所帶來的穩定與安慰便是確保眼光寬闊的唯一作法。
更從來都是「建構-拆解-重構」的過程,在每一個時間點上找到最切適的方法論之前,親手毀壞某些努力堆建的「信仰」並撕毀那些以為已經充全的論證,都是一種修行,因為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有結論的心是已死亡的、如止水般的平靜從來不存在,動態的生命也才能展現其馥郁芬芳。像都蘭的海予以的解答,關於精神與靈魂能量的源源不絕:在整體性的平和穩定之下,保有驅動性及熱忱作為生命活力,真實的平靜即是奠定於此基礎之上才得以存在。
存在主義那在有限中尋找無限的執著,同樣也擴及於時間和空間上,對於精神性擴展的追求與實踐,以這樣的形式去創造可見與不可見、有形無形⋯⋯各種層面與維度上的無限。同論文集裡說的,人是永遠活在未來的動物,我們的現在只是未來的一小部分,也正因此才得以使生命展現生氣與不朽性。
這段時間的混亂得以被平息,不僅僅是因為書與文字、樹葉與陽光。
我特別想感謝W,因為與她的所有對談及信件,僅僅是存在,便讓我堅信自己尋覓的精神與靈魂仍然存在。她像冬日裡的陽光,溫煦柔和,深遠地照進了我的精神世界大門,我對於自己有訪客感到訝異。 「原來有人會來。原來有人能夠且願意到來。」不刻意也不過分努力,就像愛丁堡四月的櫻花落花一樣,輕輕地掉落,便落在我的心頭上了。正是這種感覺。是一種又得以重新相信心臟,相信人,相信世界,相信精神。時常想起回台北前D載我去轉運站,坐在駕駛座上背對著我說的那段話:在這條內在價值與精神追求的路途上會很孤單。確實在看見這些很重要、顯明,卻大多數人無法體會、不加以關照的事物時,我甚是沮喪,也感到無力,甚至難得地孤單。可何其幸運能夠有W作為世界這場遊戲的同行者,我蓄勢待發,也充滿期待地展望未來。直至那刻我發覺,原來他者走得如此靠近心臟與腦袋是這種感受。對於能在此世有這般相遇與交集,覺得自己無論如何都被世界溫柔眷顧。
過去好多時刻存在的質疑或許隨時間流逝而消散,可其並非以積極性解決之後果被肯認,因此我仍對於新與舊的劃分、在與不在的辨別、時間與非時間性等討論有偌大疑惑。然我亦終於接納衝突與矛盾之於完美統協的可抵達性之必要,也在心裡明白若能於某特定一處,無論如何都可以找到散落的自己或世界或生命碎片,光有那個地方存在,並清楚知道自己應該去哪裡聚集與探尋…那便足夠,也遠多於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