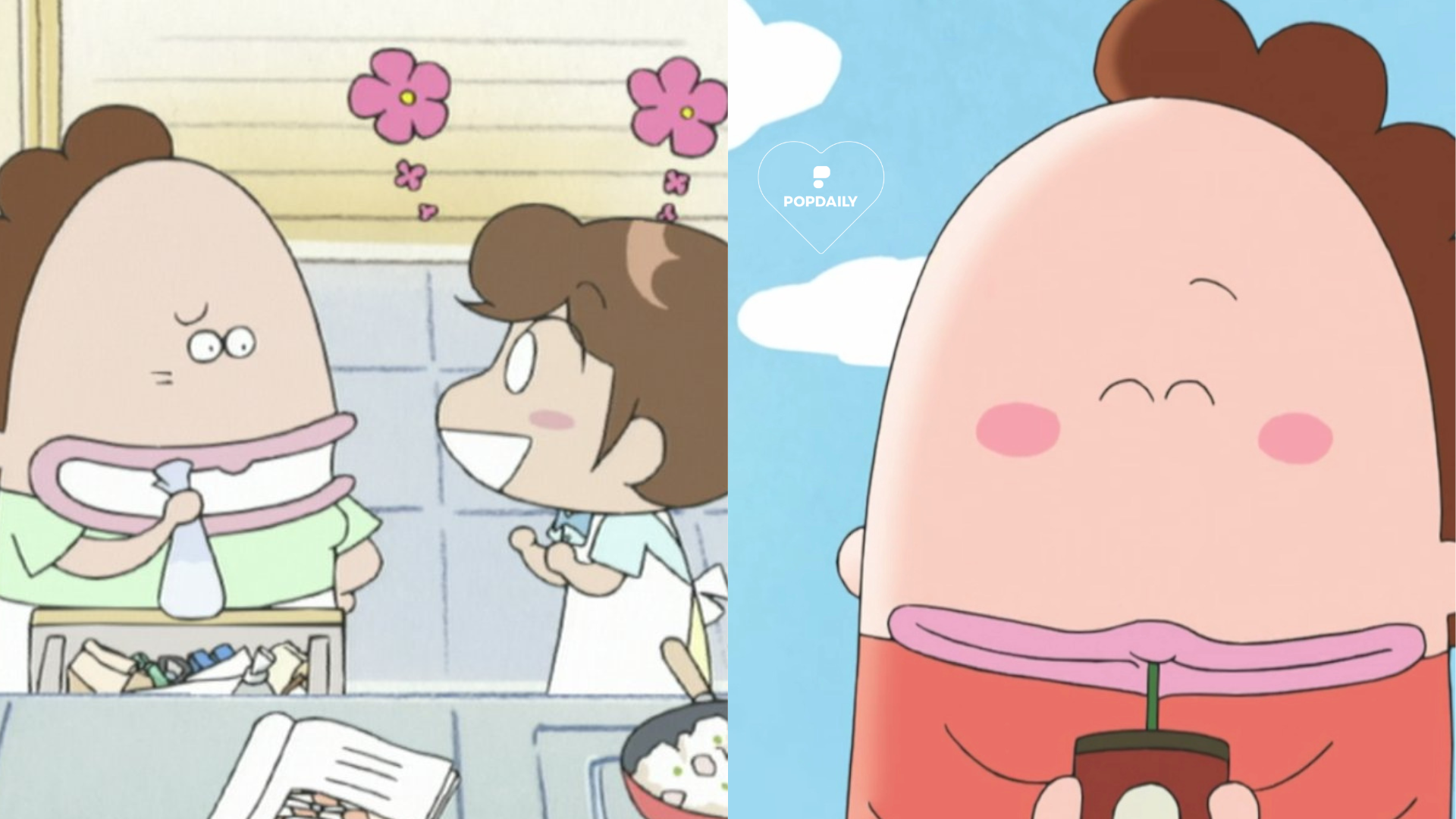關於成為字母以前最後的話
2024.10-2025.05.20
「當我與你從3900公里的距離變成一個雪隧的時間,一切的事情都容易與你勾聯。」
回台灣以後,我頻繁地搭乘客運與台鐵,足跡輾過東西南北,奔走之餘只是想看似不小心地,遺落下身上沈重的情感包袱。
北上的火車,選了個最靠近窗也能看著路漸漸遠去的位置。在區間車的窗框上看書,陽光灑在泛黃的書紙上,字字都在發光。
書裡的內容令我想起你,想起第一次與最後一次看螢火蟲都是與你。腦中播映了好多畫面,那份書寫的渴求澎湃激昂,但我知道這些只能待你成為一個字母以後,才開始書寫。關於鬆軟土壤上安靜雀躍的步伐,被植株上的露珠沾濕的腳踝,黑夜河邊草地上輕輕的吻,以及最深刻的凝視和體膚的溫度。那些話不能同你說。只能在你成為一個字母,成為我不帶傳達目的的對象以後,被書寫。為了避免帶有目的性的,複寫那些過於濃密的愛。
我想,太多時候確實愛得過分了。帶著一切的所有,攤開在你面前,沒想過要掩藏,只想給予全部,不計一切,也無法算計地將自我交予出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件事情、這種心態可能就變了。過分之中我們都變成彼此不再熟悉的模樣。可我好愛你。我對你的偏愛早已是抵抗世界般的不合理,再多都成為對在乎我的人的糟蹋。那些愛最後都成為自損,而我承擔著愛你的疼痛。
後來想想,那種狀態就像即將過熱的臨界點,再多那麼一些便會汗流浹背的炙熱,可未至該點之前,是種夾處在中間的不適感。溫暖與悶熱之間,只是一步之遙,卻左右為難。大概就是這種程度的親近,多一點會崩解,少一些卻不夠黏膩。就像那五樓的小房間,在尷尬的界點上,悶熱無風,一切嘎然而止。我們便在這樣的無時間性裡慢慢停滯,漸漸失去對世界的實感。於是日子就在這般平和的狀態裡悶燒,最後我們還是會被蒸乾,讓一切都成為過度親近的陪葬品。
這段時間我還是傷心了幾次,因為你的回應與態度受傷了幾次。很任性的、很不爭氣的還是難過。心臟裡那股淤積擁塞的感覺使我換不上氣,不適得快要把整個心臟都吐出來。我一直處在快要急哭了的邊緣,能夠給予你的耐心和寬容越來越單薄。心理上的隔閡越來越厚,百般不能理解你為何能將再次前來的我蹂躪粉碎。我永遠記得最後一次看著你的臉,那是最近又最遠的距離,遠在看見你了,卻不再能夠理解或愛惜那樣的你。
直到某天一早出發去台北時,赫然想起底下的這條路筆直下去是過去R載我離開現實一起奔至利澤海邊的路,想起這樣的意義其實已被覆蓋許久,久到我都忘了最後一次這麼想是什麼時候。因為後來它的意義成為回家。在認識你以後,在這條路上,我只想著隧道那頭外的你在等我回家。
記憶隨著時間以及生活中的幸福,像漆一樣,一層一層疊刷在上面,我想是不是有些東西始終會消失。在記憶裡、視野中都是。最後可能瀕臨我再也想不起的邊緣。所以我會繼續書寫關於你的很多事情。因為我仍然相信那些觸動是生命裡極其難得的。
有一天我定會再也想不起很多細節,我可能只會記得許多無關緊要的小事情。好比今天我仍然記得在大雨滂沱的廢棄哨站裡的那場野餐約會,R一朵水煮花椰菜都沒吃。我卻不記得更深入的對談或者深情的對視。你也一樣。隨著你與我形體和靈魂的分離,有天我必定會忘記很多曾經以為可以永遠記得,也希望永遠記得的事物。如同《挪威的森林》,關於直子的事物無可避免地在渡邊的記憶裡漸漸模糊暈散,也正是為何直子叮囑、期許渡邊永遠記得自己。我曾有過一樣的希望,但現在的我想,若能記得如同花椰菜般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許也是種可愛。能夠在記憶裡抹去你留下的很多傷痛,然後使你重新成為一個模糊卻可愛的人。我是這麽想的。那時,耳機突然隨機播放了“Apple Pie”。我想起家的感覺。再清晰不過。
前幾天回學校了。去了最喜歡的觀景平台,發現過了兩年一切景致都還是差不多的樣子。可自己真是徹徹底底地不同了。最近也聽到一首歌“Have a good summer (without me)”。就這樣我們已經分開了一年,又來到副熱帶上的夏日,潮濕黏膩,身體周圍總是裹著一層如保鮮膜般不透的濕氣。比起陰雨綿綿的冬日,眼角只剩下那一抹潮溼。這會是第二個沒能有我/你同行的夏日,我終究靠著自己成為了一個不畏光的人。新認識的人們說:「你真陽光。」我莞爾一笑,想著究竟從什麼成為了什麼。不管是什麼,也好像終於能由內而外地、正面肯認大部分的自己了。這些東西從烏雲密佈輕輕悄悄地成為透光灰雲。透明度60。新的生活很好,真的很好。多數時候我是那麼那麼地輕盈,也因此我好替那個站在觀景平台上流淚的自己感到欣慰。
忽然覺得自己再次獲得對未知的未來保有期待的能力。這是難得的。儘管關於你的一切就像暫停鍵一樣,止於那個瞬間,彷彿一切都凍結在該時該刻;沒有流水輸入使它們淤積於新生活的邊緣,沖刷著甚至掉落到視野外。你成為幾十億人口裡的小人物,我們可能再也不會見面,你也可能成為記憶裡淺淡的色彩、模糊的輪廓,但某一部分的你一定永遠地改變了我。那些部分拓印下了你的好。
五月中旬,心不在焉地不小心走向了文湖線,便心血來潮搭上棕線,回到那裡。
耳機裡單曲循環著“Dream like me”,在尚未熱得能將人蒸乾的炎炎夏日來臨前,將掛滿三色小燈籠的忠順街晃過一遍,踩著腳踏車將木新路二段一直延續到新店的路重新騎了一遍,自己逛了過去我們最喜歡的賣場,吃了固定會一起吃的幾間店。“You left your heart behind, girl. Come back and pick it up.” 那些地方那些路線佈滿了我遺落的自己,在下下午後雷陣雨之前,全部收拾好,帶走。
回台灣以後過敏好了。奇蹟似的,就在我應該最嚴重的季節,忽然地好了。淤積擁塞的心與腦也同步疏通。我好得出奇地快,生活就像急流繼續被推進向前。
祝福你在這個夏日,過得好,過得開心,過得真真切切擁有快樂。
這些是使你成為一個字母以前,最後的話。再見。
你好,E。
點播一首Dan Whitlam 和Julia Church的Satel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