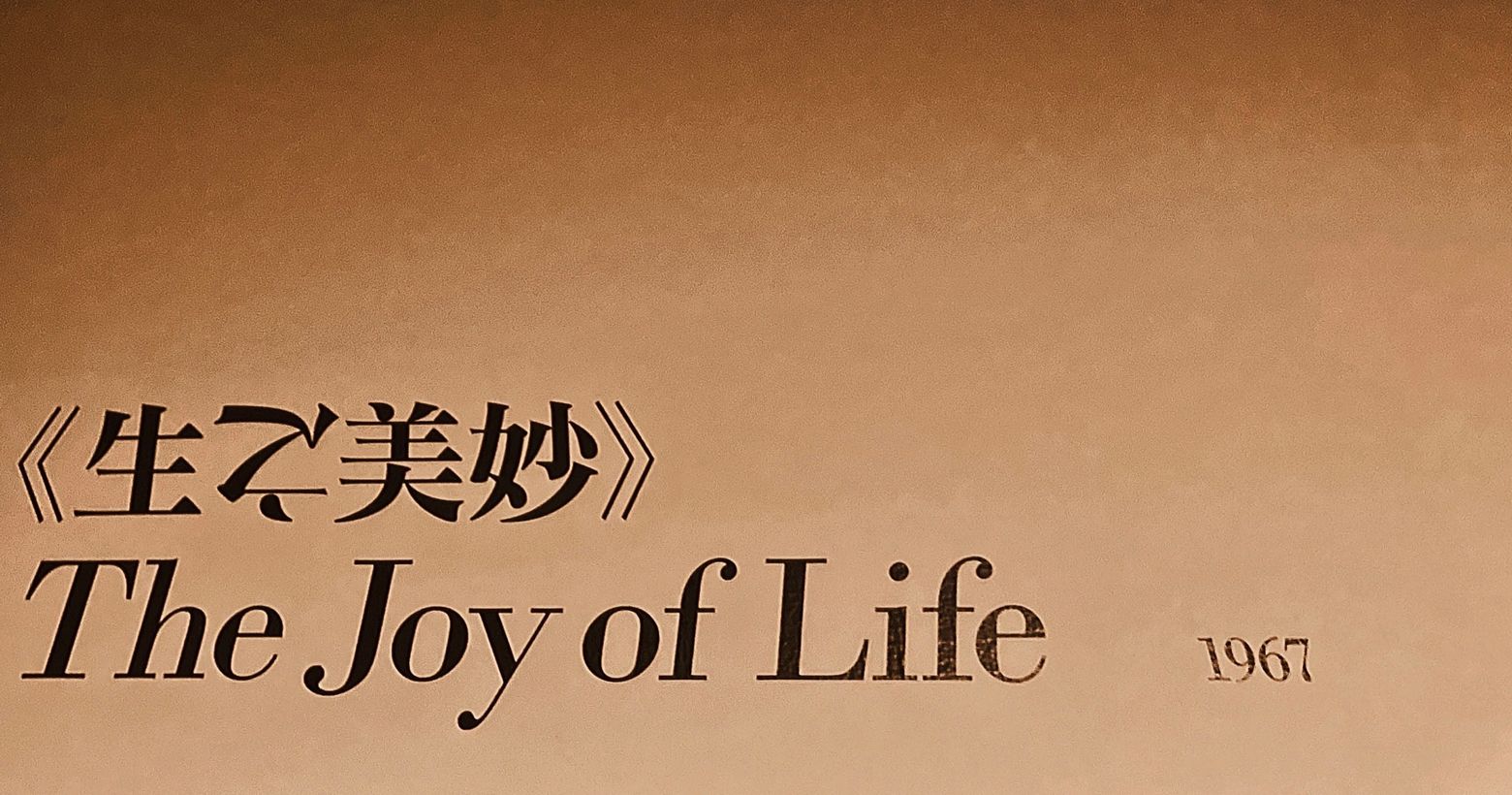關於四月相遇
2022/05/20-05/25
四月在許多文化中都有循環開始的意義,植物萌發、百花綻放都象徵重生。
然而,每年的四月之於我都很傷心,無論頻繁夢見消失的人又或者不停經歷狀態改變的拉扯。四月更總是過分刺眼,畏光的傾向使我想縮藏在陰暗的腹腔裡,躲避灼熱又刺痛的曝曬。所有朝向期許的改變也總在將要形構出輪廓之時就瓦解。那明明是象徵重生的四月,是最多花種綻放的四月,過去卻從來無法切身感受,直到今年,才第一次深刻體會到四月承載的意義。
無論是去定義又或者追求,我早就放棄持有任何一者,連面對偶爾的波動也毫不猶豫選擇視而不見。花了很多年整理那團破爛的洞窟,只得到自己完全不需要這樣的情感關係也能生活得很好的結論──甚至確信無的狀態將比有來得更好。「妳不用害怕呀,最後來到面前的他不會是他。是妳不需要害怕的他。」Z和我說過好多次,但那些已經在心裡成為固化也封閉的結論,麻痺的傷心與破碎如何能被說服。
一直以來用放棄期待的樣子過活,直到你來到我面前,帶著我所沒體會過的四月的意義。
儘管喜歡找尋定義,卻也因為無法獲得最終乾淨精確的解釋,便習慣用宿命論說明一切模糊而無法獲得清晰化的事物。這段關係也一樣。那些不可思議的體驗確立了如此感受,卻也隱微刻畫出我們將會經歷右端必然性的疼痛──因為過分緊密也不可取代。
面對著龐大且劇烈的右端必然性疼痛,不免想著過去僅有表層交集的時日,究竟能不能成為今後延續的時間額度。右端又再次像地毯般捲起,束直朝我壓倒,巨大的黑影再次遮蓋視線。「看見黑影便要記得背面有光。」這是去年年底最深刻感受到右端必然性疼痛時最終獲得的體悟。今天仍然要繼續這樣提醒自己:那些光存在,更甚至現在就已經俱足精神性的篤定。那天晚上我們便一起看見右端的光了,不是嗎?
你說忽然看見一棟海邊的房子,我說自己也曾經看過,更聽見過那個場景從未來起點的喚聲。在想像維度裡,我們各自的空間似乎總能接連到彼此那端。闔眼以後看見海在我的右邊,不是濃重黑藍的海水,不是清澈透藍的小島色海洋,是一種溫潤輕柔的藍,尾端有浪花的白色泡沫。房子在左邊,架高,淺色外觀。是木頭的,你補充道。「看見你了…手疊著或放在背後。」「是放在背後。我也看見你了,在我的左邊,你蹲著…手壓在膝蓋上。」後來朝著房子 走近,看見大窗戶,還有裏頭的陳設。腦中的畫面越來越清晰…眼皮越來越重,睡去以後不知道有沒有真正到訪了?那是遙遠的右端,時間性模糊,我卻能夠看見清晰的你。
然而,每多過一天,我越能深刻感受到自己對你,以及自身與這段關係的連結性,卻同時也知道每多過一天就距離能支持著任性的時空又更遠一些。因此把這些日子過得像煙花,卻是能延續不止的煙花。恆常璀璨,用力得讓每個當下都燃燒精光,隨後用更多橫生的新者銜接。每次都會完整回來,更彷彿下次都比前次更為完整。儘管過去時日在遙想未來抑或感受到右端必然性疼痛時會成為一種假性的可惜,但同時也深知那些經歷何其必要。「過去生命中的感受與經歷,都是為了讓我在此時與你相遇──像好久好久以前的我就一直在準備著要遇見你。」
相遇的原點幾乎沒下過雨,湛藍中滿是清澈的光,那是四月的天空。生活中多出了棕橘、黑白灰以外的顏色,綻放的花盈滿視野,那是多彩的四月。過去從沒想過自己能夠以如此明亮、高彩度的樣子存在著,直到遇見你,此時抑或右端都充盈飽和的亮光。在亮光背後,遙遠的右端,時間性模糊,我又再一次看見清晰的你。
We found each other under an April 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