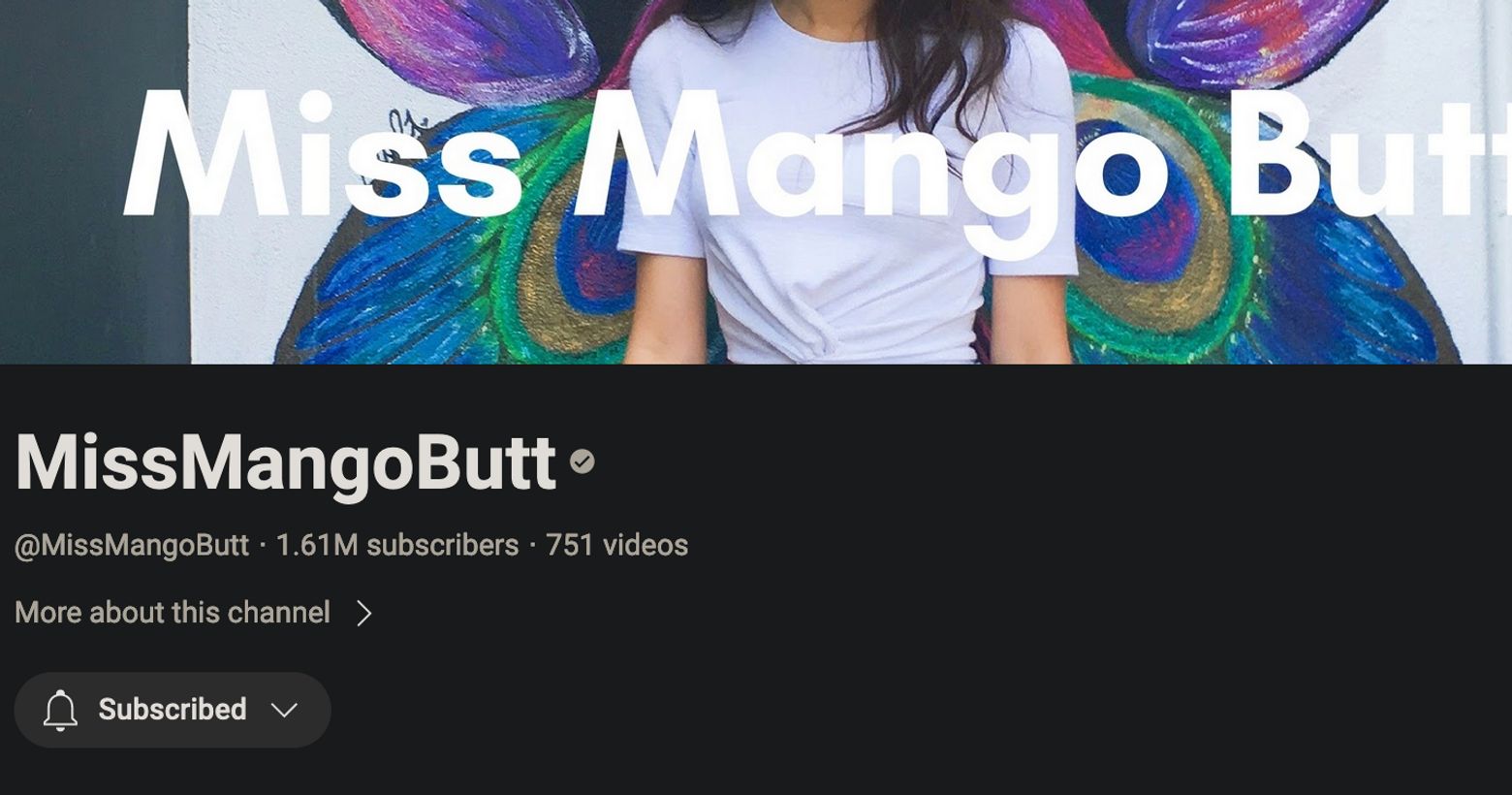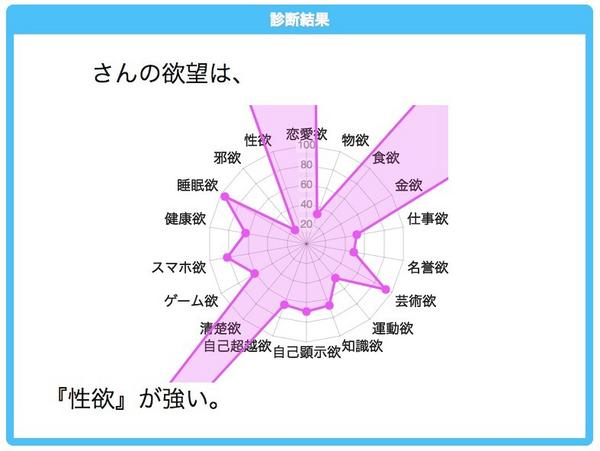關於無法縫合的洞口
2021/10/09-2021/10/11
那天嚴重的失眠,並非翻來覆去的那種,是懸吊在醒與不醒的臨界點上,能夠微微睜眼,身體卻無法動彈的那種狀態。我很清楚自己是非常疲憊的,感受得到身體不停的往床鋪的中心下陷,卻同時也感受到精神的不安定。想必是下午四點喝咖啡的任性行為讓自己陷入這般艱難的處境。
那晚在進入艱難處境前,躺在床上和他說了很多話。本來想在收完行李後寫寫信,卻因為自己的拖延而只能捨棄此計劃。我大略訴說了整天的心情起伏,包括衝動行事的部分以及過程中發掘出的隱藏自我。「我以為自己很能夠瀟灑坦然,但其實隻身一人時,總是不敢冒險。」並不是畏懼隻身,而其實享受,只是多少存在隱藏的焦慮與不勇敢。甚至有時候當我意識到快要接不住自己時,寧可將自我拋擲到無人的遠方。獨影的寂寞讓那種蝗災般撲面而來的,感受,能夠在關係層面上將負擔減輕至最低。我太相信自己,又太相信地不相信自己。「你知道嗎,那天Z跟我說,在她眼中的我就像課堂上談及的『完整的人』。她說我擁有那種形貌。而經驗過被無條件、無私的愛所包覆,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前提。」當自己聽到這段話時,他隨即出現在腦中。那瞬間我忍不住哭了,顫抖的說出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他那麼重要,但也因此使他的離開讓我的痛苦這麼深遠悠長。
何止是我。前幾天L(我從來沒有以L代稱過他,提及時向來都用最簡單的「他」,可此篇文中包含的兩個角色若都以「他」稱呼,讀者大概會混亂得無法理解吧?)在群組傳了李宗盛的《新寫的舊歌》,直到搭上離開家鄉的客運才點開影片連結。那種情感濃烈又衝動的淚水絲毫沒有被隱忍住的可能,坐在客運的第一排,在離開家的路上,聽著L傳的歌,啜泣著想念在我們生活中留下巨大空洞然後離去的他。我相信L和我一樣曾經嘗試縫起那個洞口,風吹過就呼呼作響,什麼都裝不了卻又不得安寧的深淵。我們確實嘗試過,可是無論針法多麽細緻,有時候只是開口說句話,線頭就會從頭到尾地鬆開。那些情緒又從巨大的洞口散出來。無論清醒或者沈睡,我們的洞口邊時常一片狼藉。
每次翻看愛情社會學的第十一章的講義時總是輕易鼻酸。「面對起初愛戀對象的力量及其失去,自我有一種回應方式,就是投入(introjection)、內化(internalization)、認同(identification)之,意即把他們放到心理中,成為自我的一部分。」這是佛洛依德所謂食人族式的包含吸收(cannibalistic incorporation),把失去了的你放到我心裡,永遠存在我心裡,成為構成我的一部分。有時候我確實會這樣安慰自己,可多數時候實在沒法在每次傷心時說服自己他就扎扎實實的藏在這裡。有時候甚至痛苦到瀕臨碎裂時,只有在看到洞口才能再次確認他的曾經存在。如果通過食人族式的包含吸收使他能存在於我之中的話,我和L心中就不會留有縫不緊的洞口了。不是嗎。
最後我哭著告訴他,近日的自己相對過往更深刻感受到生活裡自己所擁有的愛,所以不要擔心。雖然很多時候內心會質疑自己能否有資格接受這樣的愛,但我說自己會努力把生活過好,讓自己成為心中認為有資格接受愛的樣子。「學習讓自己能夠安心地去完全擁有。」或許多數時候依然不能夠放心接受,但我知道自己在努力改變了。就像回家。針對這件事心態上確實已經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當這次離開家時,打從心底感受到不捨—並不是因為想逃避應該面對的責任而渴望繼續窩藏,而是主動的、正面的想要留在「家」這個環境裡。
「在這裡的我會努力變得更好,也會更用力的去愛、照顧他們,而你在那裡也要好好照顧她。我們一起守護他們,讓那裡和這裡的生命用愛連成一條線,創造一個安全的網。」我愛你,我對他說。也一如始終的想念。
附上:李宗盛《新寫的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