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 - 乾燥花|1|
今天也是飄著如絲般細軟的雨,大門因為有些老舊需要施力壓一下才能完全鎖上,到了現在你依然拿捏不到關起那扇門的巧勁,於是留下半掩的門,傳了一則訊息要我下樓關門,我看著路燈沿著門縫闖入,把雨也帶了進來,掛在大門口的乾燥花擅自介入光的流動中,試圖在影子的世界把自己淋濕,什麼都和我們的第一天一樣,只是所有的細節都褪色了,彷彿是一種暗示。
「已經可有可無了。」我不確定你是否有聽見,但我試圖傳達這件事。
不明說是因為你總是想追根究底,但所有的原因你一定能在分開之後明白,最終你又想以沈默結束爭吵,又一次決定把問題留給未來,把眼淚留給入睡之後的夜晚。
「不是我也沒關係吧。」我還是脫口說出了那句話,因為我討厭你總是把話淤積在喉嚨,你肯定也已經討厭我了,那麼或許我們也都不需要再努力了。
你看著我什麼也沒說,近乎奪匡而出的眼淚在眼中打轉,我知道你已讀懂了我的潛台詞,許久不見的默契,竟然發生在這種時候。
你一昧地收著散落在房間各個角落的私人物品,我坐在床上看著你一個人忙碌,我觀察著你的視線,確認早已失去我的存在,你毫不猶豫的收拾態度,彷彿那些屬於你的東西,都有著只有妳能指認的顏色,我將額頭輕輕靠在彎曲的雙膝上,雙臂自然地抱住腿,為自己製造一個空間躲了進去,閉上雙眼,聆聽一切倒數的聲音,而現在要告別的剩你移動的腳步了。
你關上房間的門,我們的離別並沒有伴隨任何激烈的情緒,這讓所有的平靜顯得詭異。
五年了,最後證實相處的時間並不是關係延續的絕對值,走到了臨界點的兩個人,會不自覺失去產生對白的能力,即使在同一個空間面對面的相處,卻只能上演獨角戲,我們看著對方就像看著兩部無聲電影,即使讀懂唇語也無法搭配上正確的音調。
想不透為什麼這些爭吵的畫面會如此清晰,那些無話不談的片段,是什麼時候開始覆蓋上難以讀取的雜訊?一瞬間我領悟到現實的殘酷,快樂不是離去,而是不爭氣的被痛苦淹沒了,但更殘忍的是即使如此我也無能為力。
我關上大門的巨響切斷了你與我之間的關聯,你的離開就像是早已準備好一樣,沒有留下任何重新來過的機會,我回到房間將四肢展開躺平在床上,房間裡的空氣像釋出空氣的氣球,放心的卸下所有緊繃,我被這樣舒緩的氣息包覆,想像自己是一隻水母,沒有大腦、沒有心臟、沒有骨頭,支撐我的是大海的浮力,如果我們以水母的樣子再度相遇,是否就能對今天的一切荒唐一笑置之了?
我想著你生氣時拿著枕頭洩憤的樣子、無奈時面癱的五官、焦躁時皺起的眉心,成為水母之後討厭的感覺變得輕盈甚至接近喜歡,原來所有事物的象徵,只是一種心境變化附屬的隨機反應,喜歡可以是討厭,討厭也可以說是喜歡,正與反的兩岸其實也源自同一個地方吧?
作為水母我思考的事情已經太過複雜,這提醒著我生而為人的本性,人總是想用思緒控制一切,實際上卻時常被思緒控制。
「不是你就好了。」在你離開之後數日我曾經這麼想,如果不是你,那些曾經和你一同擁有的東西,或許就不會像生了病一樣,逐漸淡去原來的色彩,如今都已變得蒼白。
這個過程像是溫水煮青蛙,那些被我們所染過的日常,在我感到不對勁時就已經逐漸沒了生氣,所有觸碰過我們回憶的顏色,也在我察覺之前沒有痛苦的原地死去。
我沒有怪你,也不想去接觸存在彼此痕跡的過去,只是一天過一天,重複規律的生活,讓自己對所有的變動感到麻木,在這個失衡的世界裡長出新的習慣。
有時候看著那些失去彩色的地方,仍會湧起一絲的惋惜,邊看著這一切黯淡邊想著,或許失去的顏色會從此永遠離去,不過因此成為一半的色盲,也算是一種與你的緣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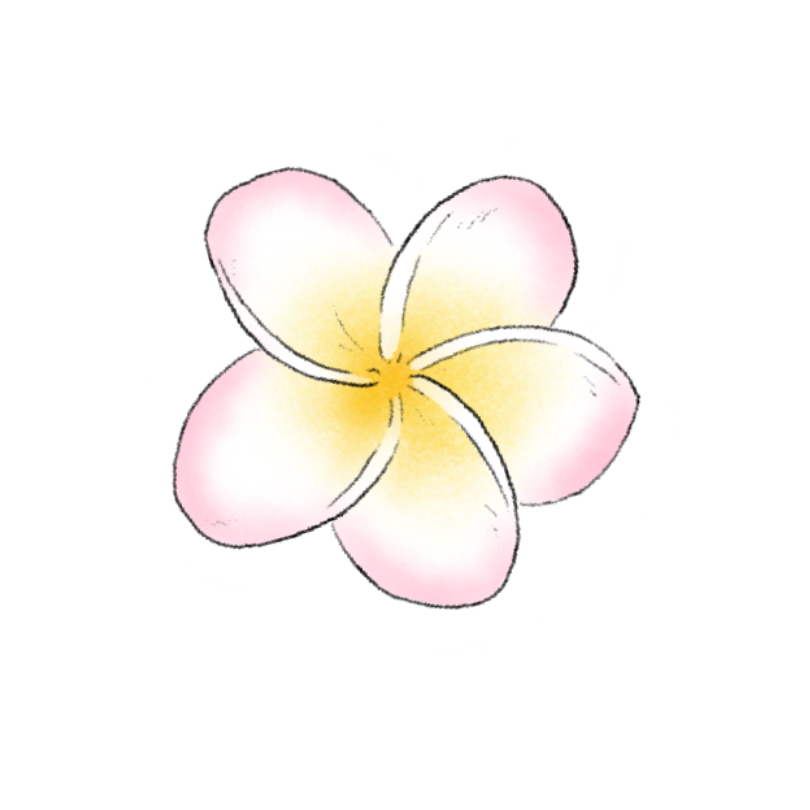
星期六的下午我意外的想到附近的社區公園走走,大概是受到太陽的召喚,我想將自己拎出去曬一曬,連日的降雨讓整個城市被水氣包覆而變得難以呼吸,身體累積了一個禮拜的濕氣,終於得到機會一次排除,即便假日下午的公園會被這附近住家的孩子們霸佔,不過為了這久違的陽光,我還是想出去看一看。
你離開後我重新點起了菸,混合著來日的濕氣時間變得黏稠,尼古丁產生的暈眩讓我有時以為你還在,但房間空盪著一人的冰冷,雙人床的右側、餐桌的對面都不再有溫度,這時我會再點起一根菸,讓濃烈的白煙炙熱我所嚥下的每口空氣。
浸潤在菸草之中讓我想念陽光的味道,期待那份溫煦能充滿我的肺葉,搖曳的窗簾洩漏風的行蹤,半開的窗已經準備好迎接陽光,午後的陽光是還沒那麼成熟的金黃,隨著雲的散去而淡入房間裡,一部分映照到我身上,光影在我手中流動,窗外孩子們嘻鬧的聲音也隨之流了進來,鳥群也因為天氣放晴,而開始回到公園附近聚集,所有的聲音讓外面的世界再次活絡起來,我更加感受到這份熱情的呼喚,毫不猶豫穿上了鞋走出房間,迫不及待融入在這久違的溫暖中。
每次到公園已很久以前失眠的夜晚,你會和我一起到公園散步,買旁邊便利超商的冰淇淋交換食用,而在你離開之後公園也因此沒了顏色,這是讓我最惋惜的事,初次來到公園時雞蛋花還未長出花來,但你一眼就認出這是雞蛋花,因為你奶奶家種了一棵。
「奶奶希望我的心可以像雞蛋花一樣綻放,發出溫暖內斂的光。」你告訴我雞蛋花的樣子,順便用手機上網找了圖片給我看,但搜尋出來的圖片有白黃也有粉黃的花,我問你花圃中的雞蛋花會開出哪種,你說只有等它開出來才知道,於是我們一人猜一種,卻也不知不覺的一起忘了這場賭注。
之後,失眠的夜晚逐漸有了其他事替代度過,公園不再是個絕對的選項,雞蛋花開了又謝,即使想起了這段過往,也沒有了能一起產生共鳴的人,有些事遺忘後是找不回來的,像查無此人的信件,最終是走散了歸去的方向。
「碰!」我感到右腿後方膝蓋處被撞了一下,雖然力道不大卻還是讓我的膝蓋拐了一下,我轉過身是一位小女孩,手中拿著各種不同的花,即使沒了顏色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藏在其中的雞蛋花,那是個暗示。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女孩低著頭迅速向我道歉,表情有些愧疚。
我看著女孩手中的花,等不及抓住這個機會說:「沒關係,但你能告訴我這朵花是什麼顏色的嗎?」
「你看不見顏色嗎?」女孩抬起頭,透著光的雙眼帶著些許疑惑,似乎是第一次真正認知世界上有看不見色彩的人。
這時女孩的母親碎步介入我們的對話,搭著女孩的肩又和我再次說了對不起,然後帶著女孩離開,我望著他們,女孩似乎感覺到我的視線,他回過頭看了我一眼,卻什麼也沒說的走了。
的確,不是每個浮上心頭的疑問都能得到解答。
「為什麼總是我?」我想起你哭的時候時常問我這個問題,但如果我知道為什麼,你大概就不會這樣問我了吧?
最終你也真的不再問了,那些「為什麼」被你打包進行李廂,或許帶給下一個對象,或許在重新整理行李時,跟著那些我送你的禮物一同捨去,無論腦中浮現多少種假設,事實上都已與我無關,我再也不會因為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而惹哭誰了。
我想找到那棵雞蛋花。
沿著公園放射狀的走道尋找,在黑白的世界,只能依靠記憶和線條輪廓來指認,我來回找了兩次,連現實也認為這是一場徒勞無功,呼吸因為不斷移動而變得急促,我幾乎是快要放棄這看似沒有意義的追尋,剛好出現的長椅,讓我決定在此佇足休息片刻。
癱坐在長椅上時,耳邊不時傳來公園遊樂場中孩童們嘻鬧的叫聲,我望著對面的花圃發呆,不時有人從我面前走過,時間被他們的來去不斷帶走,而我還停在這裡,想著這個永久固色的黑與白什麼時候會結束。
時間用天空的顏色說明它流逝,該回去了,無功而返已成為一種見怪不怪的人生常態,起身時我踩到了鞋帶,還好與生俱來的平衡感拯救差點跌落的身體,重新站穩後我蹲下身綁了鞋帶,抬頭的瞬間,一個直覺要我重新整理視線所及的一切,眼前不遠處有一朵落在水泥磚上的花,我認出了那個熟悉的輪廓,就像當初你馬上認出雞蛋花一樣,前方水泥磚上的雞蛋花,倒映在我眼中重疊了兩段時間。
我趕緊向前,完全沒有思考或許自己走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幅黑白的素描寫真,也大概是這樣不帶任何遲疑的心,當我拾起花的那一刻,顏色從花的中央長了出來,我真實的體會了電影中破除邪惡巫師魔咒的奇幻情節。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花,期待顏色給予最直接的答案,但世界永遠是不按牌理出牌,花既不是想像中帶著純粹的白黃,或鮮豔奪目的粉黃,而是白黃之外暈染上剛剛好的淡粉色,清新脫俗的樣子像是初次接觸妝容,只抹上淡雅胭脂的少女。
公園也同時逐漸恢復了顏色,原來公園的顏色這個樣子,我帶著陌生的心情看著這個甚是熟悉的地方,在夕陽之下,面光的細節裡反射出不同深淺的金黃,灰色的水泥磚走道也變得閃閃發光,紅色、綠色、藍色此起彼落震動著胸口深處,第一次感覺到色彩的喧鬧其實是一件這麼美好事。
遺忘與憶起之間的落差,讓原來不起眼的日常光景變得光彩奪目,我閉上雙眼,心中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油然而生一抹柔暖,我輕握著剛剛地上的雞蛋花,掌心將所有閃現的回憶包覆,我看著即將落下的夕陽,與此刻所有同在的事物,一同慶祝這燦爛的一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