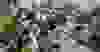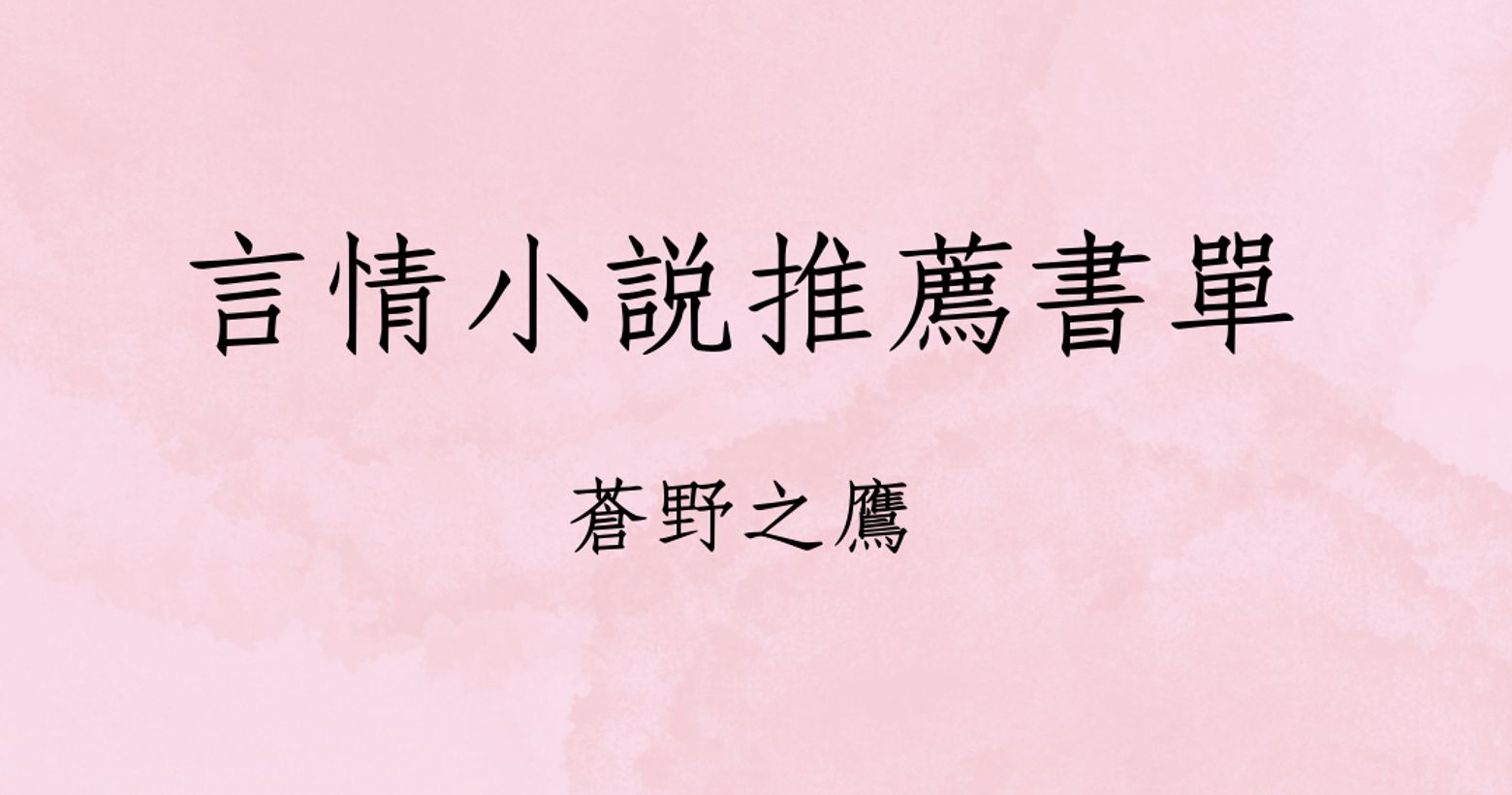焦陽溪神傳--罪人的祈禱3
畫室的老師是個像猴子一樣跳來跳去嘰哩呱啦講個不停的三十歲男子簡欽彥,現在他正揮舞著已經變成棗泥色的手指,描述他當年上台北考兩個藝大時的辛酸血淚:「台北的冬天多冷呀!尤其關渡那間,還在山上,根本是冰箱!我一個台南人衣櫃裡不超過三件長袖的差點被冷死,那個面試的教授看我一直抖,從頭到尾都在跟我聊天氣……。」
「聊天氣?」一個厚嘴唇圓眼睛的女孩錯愕地問道。


「對呀!我跟你們說如果以後如果要考北藝一定要記得多拜拜,運氣屬性要點滿!老師我國高中六年每年都拿學生美展的沒上,另一個吊兒啷噹的同學,成績也沒多好,穿了一身嬰兒粉黃色連身衣去面試,唱他阿嬤的搖籃曲居然拿九十幾分,沒人知道他們的標準是什麼……。」簡欽彥一系列誇張的表演把這群正在跟廉價水彩紙肉博的學生們逗得哈哈笑。
王伯耘非常努力地拿捏著渲染乾掉的時間點,但是那該死的考試指定用紙就是打死都不吸水也不顯色,硬是讓該清楚的地方通通糊成一團,同樣的動作在隔壁房高中組的頂級法國紙上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們一水一風兩個神明盡了全力助攻他在時間內畫好練習,效果卻有限得很,一張爛紙弄死了兩個神明呀!


王伯耘在九點整的夜色中坐上了回到油口的公車,他還沒有讀任何一科明天要考的東西,但現在學校的期末考遠遠沒有迫在眉睫的寒假術科大考重要,他沒有比賽紀錄又不是原住民,要吊上蘭中、青榕或大正美術班的車尾就只能靠這局了。
接下來幾個禮拜,只要清元一得空我們就到人界跟著王伯耘,找到機會就施展各種作妖式的浮誇助攻。盯著他上課,考試的時候提醒他,畫圖練字的時候幫他控制水份,只是這個寫字奇醜的孩子再怎麼書法也還是慘不忍睹,我們三個最後都放棄了這個項目。
這段短暫的時間裡,多虧了分開在不同的系統裡生活讓我們有聊不完的話題,我對劉奕行收賄的感冒在看遍了人間骯髒事的他眼裡,像是一種來自井蛙的大驚小怪。自從我回來之後,清元對基督教的敵意就消失無蹤了,就算告訴他我是因為吳墾推卸責任成功才被踢出來,他也不以為意,甚至還很想找門路去看看郭啟泰一家呢!
***


農曆新年前夕一個晴空萬里的早晨,蘭港高中門口擺著寥寥幾攤考試用美術用品的攤位,李孟丹經過攤子,又讓王伯耘檢查了用具一番,才比他還緊張地衝上公布欄找他的考場。
入場前,王伯耘在走廊上一邊嚼著水煎包一邊複習下午的筆試美術史,腎上腺素比兒子還發達的李孟丹正在用珠連砲似的叮嚀要兒子記得老師說過畫面要保持乾淨不要糊糊的、鉛筆進去之前要先削尖、撕紙膠帶要小心不要撕破畫面、開始前要記得先上廁所……等等,活像這半年來上畫室補習的都是她一樣,把王伯耘煩得一肚子火。
第一堂素描,水神跟風神都愛莫能助的項目;只能靠他自己的一場考試,好久不見的紙紮人玉女在王伯耘撕下邊角的膠帶交卷時短暫地出現在考場一下子,確認他交的試卷背面有寫名字後就消失了。


「你說玉女會去告密我們來這嗎?」
「嘖……。」清元皺起眉頭「反正我們是來幫他的,如果他們來了再說吧。」
第二堂水彩,教室的門窗都是上鎖的,不通風的情況下我們也助攻不了太多,但是已經跟爛紙相處了一整個學期的王伯耘可謂有備而來,似乎是聽了畫室老師說打分數的時間很短,評分老師不會花很多時間去看細節的關係,打完底稿後他就把毛刷刮到最乾,調了個極淺色,直接跳過渲染的步驟用乾刷淺色代替,這下把所有等紙乾的時間都省下來了,其他考生在處理渲染半乾的區域時他已經在畫重點了。要結束時換金童來快速巡了一下他的姓名欄。
午餐時間,李孟丹一邊繼續她神經質的叨唸,一邊往兒子腿上又是便當又是優酪乳地塞,我們正在思考要怎麼讓她閉嘴的時候清元懷裡發出五色鳥的陶笛聲,精神抖擻地吹著台味十足的勵志老歌愛拚才會贏:「一時失志無免怨嘆〜一時落魄無免膽寒〜……」


他掏出包了五色鳥陶片的護身符塑膠套,穿有紅棉線能掛著當項鍊的那種,從塑膠套裡捏出折成銅錢形狀的符紙,打開了來自關公的語音留言:「清ㄟ〜菲律賓那邊有消息了,我們都要過去,麻煩你回來幫湘ㄟ顧一下後面。」
「我要回去顧後廟,你如果遇到王家人或其他什麼事情就直接先回我家,知道嗎?」
一整個下午清元都沒有再回來,我陪著考完最後一堂書法的王伯耘走出考場,很幸運地他這次揮毫能讓人辨認得出哪個字是哪個字。
麻煩出現在回家的路上,從大城市回鄉過年的車潮擠進了從蘭港市往油口鄉的路段,塞車,瞬間糟起來的空氣把母子兩薰得發昏,也就是在這時候,王修和金童玉女從母子倆的身體走出來,出現在停停走走的車陣中。


「我是王伯耘的曾曾叔公,你是?」王修看著被王伯耘全副武裝的我,警戒著問道。
「我是焦陽溪,半年前拜訪過王會厝的溪神。」事到如今還是招了吧。
「……你就是伯耘畫的那個機器人?」王修瞇起眼睛上下打量我。
「嗯……。怎麼了嗎?他給我畫了這身工具,我想謝謝他才來陪考的。」
「不需要!當初你們答應了不會再來碰王家後嗣的,最近伯耘在學校那些不勞而獲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你做的?」
「不勞而獲?他給了我生命力和工具,我幫他也是他應得的,不過分吧?」
「這是強詞奪理,你現在讓他覺得畫畫圖信個假神就能有好運,這是在慣壞我們的孩子。」


假神這兩個字讓我聽了很不舒服,我可是你們王家母子倆信出來的你好意思說我假。
「喔!不好意思喔!我還不知道你們王家有這麼在乎教育呢!我以為如果你們有把子孫教得聰明一點,娶到的媳婦就不會到處亂拜,就不會有來路不明的神明來跟你們搶功勞了。想想我也是李孟丹生的,也是你們王家的一份子,講話何必這麼生分呢?曾曾叔公!」這時候車潮稍微疏通了些,我們在行進的車潮中吵了起來。
「你還在強詞奪理!」王修生氣了「我們當初說好了兩不相欠,你們不會再來碰孟丹跟伯耘的,一個人造的假神野鬼自己毀約還跟我講這些……。」


「我講錯什麼了嗎?」我不高興地打斷他「你們如果有把自己的子孫教好我就不會被生出來了不是嗎?我是無辜被創造的,來餬口飯吃也要被責怪?這到底要怪誰?我看別人家教出來的子孫就哥哥弟弟各有所長、爸爸疼妻兒、媽媽又賢慧又能幹,你們教出來的東西呢?如果你們有本事把自己的子孫教好,我就不會存在,你們就不用跟我這種假神野鬼計較,王得榮也不會簽賭,王伯耘就不會被欺負,王月琴也不會未婚懷孕偷錢殺孩子!你說這應該怪誰?」
「你講這什麼話!吃我們家的飯還嫌我家的菜,現在是你來靠我們王家人過活你好意思講這種話,要不要臉?」王修緊握著拳頭,面紅耳赤地咆嘯道:「別人家的子孫那麼好你不會去那個好棒的別人家蹭信仰?回來找伯耘作什麼?在好人家討不到飯吃嗎?」


「喔厚厚!喔我的天吶哈哈哈!」我氣得笑聲和淚水同時衝出了五官「對!我就是討不到飯才得來你家,你還知道自己是挑剩的呀!要是能去好人家討生活,我也想呀!我多想呀!就可惜別人家的子孫跟你們家的不一樣,不會蠢到隨便看到一條溪就覺得裡面有神快拜!還付錢!人家的祖先在活著的時候就把他們教好了!人家的幸福跟優秀是世襲的!就跟你們家的愚蠢一樣!代代相傳!」
王修和金童玉女同時撲上來,他們的個頭都比我大得多,我用王伯耘畫給我的裝甲和水砲對抗這三個王家人長年用紙張和線香燒出來的存在,戰得難分難捨。
我用盡全力跟他們拚搏,一點也不想退讓,不想逃跑或離開。討飯也好,不要臉也罷,我就是跟定了王伯耘他全家!王得榮夫妻的罪惡和愚昧,是我被生在一片荒蕪困窘的灰色中,被迫參與這場生存遊戲的根本原因,不跟他們討我要跟誰討?


冬日的夜色來得早,天越黑,越往油口靠近,車流便越順暢,亢奮、緊繃了一整天的李孟丹母子現在都有些累了,車聲壓過了兩人肚子的咕嚕聲,王伯耘在母親身後打著盹,李孟丹想著也許今晚在外面買就好了,就吃炸雞和披薩吧!慰勞慰勞考了一整天的兒子,吃完也不用洗,話說今天又是一個要收衣服的日子呢!
她在一個巨大的十字路口旁停下來。
我們四個從車子後方打到大馬路上,金童玉女已經被我轟得四肢濕軟,王修把我按在地上阻止我發射水砲,我掙脫的時候正好刮起了一陣風,扭打中我的水砲打中了撲過來的金童,他摔出去的軌跡揚起了幾粒沙塵,沙塵順著風飛進了李孟丹雙眼,就在她閉上眼的瞬間,她身旁的兩台機車闖紅燈飆了出去,她聽到身旁出發的引擎聲以為綠燈亮了,因為害怕被後方的大車按喇叭催趕,就瞇著眼跟著騎了出去。


等她總算清掉沙塵睜開眼的時候,卻已經是生離死別的瞬間。
煞車聲和喇叭聲劃破天際,畫筆、調色盤、筆洗、鉛筆、軟橡皮和噴膠甩到了入夜的馬路上,用了一半的紙膠帶沿著回家的方向歪歪扭扭地滾呀滾,直到被一台趕著回家過年的車子輾扁在地上。
(待續......)